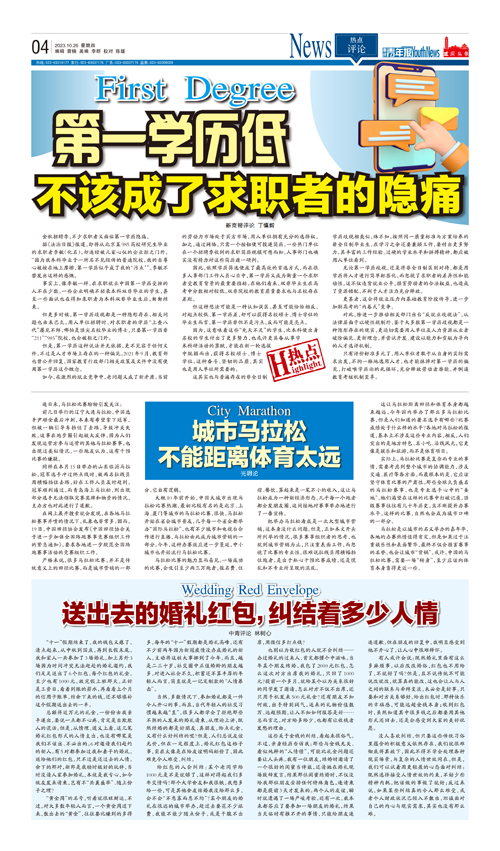新京报评论 丁慎毅
金秋招聘季,不少求职者又面临第一学历隐痛。
据《法治日报》报道,即将从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毕业的求职者李敏(化名),却连续被几家心仪的企业拒之门外,“因为我本科毕业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院校,我的自尊心被按在地上摩擦,第一学历似乎成了我的‘污点’”。李敏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事实上,像李敏一样,在求职就业中因第一学历受挫的人不在少数。一些企业明确不招录本科双非毕业的学生,甚至一些面试也在得知求职者为本科双非毕业生后,匆匆结束。
但更多时候,第一学历歧视都是一种隐形存在,相关问题也由来已久。用人单位招聘时,对求职者的学历“上查八代”屡见不鲜,哪怕是顶尖名校毕业的博士,只要第一学历非“211”“985”院校,也会被拒之门外。
但是,第一学历这种说法并无依据,更不见容于任何文件,不过是人才市场上存在的一种偏见。2021年9月,教育部也曾公开回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
如今,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老问题又成了新矛盾。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用人单位拥有充分的选择权。加之,通过网络,只需一个按钮便可投递简历,一些热门单位在一个招聘季收到的求职简历规模可想而知,人事部门也确实没有精力对这些简历逐一研判。
因此,依照学历筛选便成了最高效的首选方式,而在很多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心目中,第一学历又成为衡量一个求职者受教育背景的最重要指标。在他们看来,双非毕业生在高考中分数相对较低,双非院校的教育质量要求也与名校存在差距。
但这种想法可能是一种认知误区。甚至可能恰恰相反,对起点较低、第一学历差,却可以获得名校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而言,第一学历非但不是污点,反而可能是亮点。
因为,这意味着这些“先天不足”的学生,比本科便出身名校的学生付出了更多努力,也或许更具备从事学术科研活动的禀赋,才能在新一轮选拔中脱颖而出,获得名校硕士、博士学位。这种奋斗、坚韧的品质,其实也是用人单位所需要的。
这其实也与普遍存在的非全日制学历歧视相类似。殊不知,按照同一质量标准与方案培养的非全日制毕业生,在学习之余还要兼顾工作,要付出更多努力,其丰富的工作经验、过硬的学业水平和拼搏精神,都应被用人单位看到。
无论第一学历歧视,还是将非全日制区别对待,都是用学历将人才进行简单标签化,而忽视了求职者的差异性和能动性。这不仅违背就业公平,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造成了资源错配,不利于人才活力充分释放。
更甚者,这会将就业压力向基础教育阶段传导,进一步加剧高考的“内卷式”竞争。
对此,除进一步推动相关部门出台“反就业歧视法”,从法律层面予以硬性规制外,鉴于大多数第一学历歧视都是一种隐形存在的现实,更迫切需要用人单位及人力资源从业者破除偏见、更新理念,并尝试开发、建设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选评机制。
只有评价标准多元了,用人单位才敢于从自身的实际需求出发,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也才能抹掉对第一学历的偏见,打破唯学历论的死循环,充分释放劳动者潜能,并倒逼教育考核机制变革。
光明论
连日来,马拉松比赛纷纷引发关注:
前几日举行的辽宁大连马拉松,中国选手尹顺金最后冲刺,本来有希望拿下冠军,但被一辆引导车挡住了去路,导致冲关失败。这事在跑步圈引起极大反弹,因为人们发现运营方参与运营的其他马拉松赛事,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一些跑友认为,这有干预比赛的嫌疑。
同样在本月15日举办的山东临沂马拉松,冠军选手冲过终点线时,被两名拉线员用横幅挡住去路,好在工作人员及时赶到,冠军顺利通过。而青岛海上马拉松,则出现部分选手无法领取完赛奖牌和物资的情况,主办方也对此进行了道歉。
在网上展开搜索就会发现,在各地马拉松赛事井喷的情况下,乱象也非常多。因而,19日,中国田径协会发布《中国田径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路跑赛事竞赛组织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规范全国路跑赛事活动的竞赛组织工作。
严格来说,很多马拉松比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田径比赛,而是城市营销的一部分,它自有逻辑。
大概10年前开始,中国大城市出现马拉松比赛热潮,最初比较有名的是北京、上海、厦门等城市的马拉松比赛,很快,马拉松开始在省会城市普及,几乎每一个省会都举办“国际马拉松”,也有不少城市和电视台合作进行直播,马拉松由此成为城市营销的一部分。今年,这种办赛效应进一步蔓延,中小城市也开始流行马拉松比赛。
马拉松比赛的魅力显而易见。一场成功的比赛,会吸引至少两三万跑者。报名费、住宿、餐饮,算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让马拉松成为一种新经济形态。几乎每一个跑者都会发朋友圈,这间接地对赛事举办地进行了一番宣传。
把举办马拉松看成是一次大型城市营销,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正如本文开头所列举的情况,很多赛事组织者的思考,也就到城市营销为止,只注重表面工作,而忽视了比赛的专业性。很难说拉线员用横幅挡住跑者,是出于私心干预比赛成绩,还是慌乱和不专业所呈现的混乱。
这让马拉松距离田径和体育本身都越来越远。今年国内举办了那么多马拉松比赛,但是人们知道的著名选手有哪些?比赛成绩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各地对马拉松的报道,基本上不涉及这些专业内容,相反,人们突出的是地方特色、名小吃、沿线风光,它更像是娱乐和旅游,而不是体育项目。
实际上,马拉松比赛是复杂而专业的事情,需要考虑到整个城市的协调能力,涉及交通、医疗等各方面。而最根本的是,它应该坚守体育比赛的严肃性。那些全球久负盛名的马拉松赛事,也是专业选手心中的“圣地”,他们渴望在这样的比赛中打破记录。顶级赛事往往有几十年历史,且不断提升办赛水平,这样的比赛,自然也会成为城市口碑的一部分。
马拉松是以城市的名义举办的嘉年华,各地的办赛热情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过于注重娱乐性和表面繁华,最终不仅会损害赛事的名誉,也会让城市“背锅”。或许,中国的马拉松比赛,需要一场“转身”,至少应该向体育本身靠得更近一些。
中青评论 林树心
“十一”假期结束了,我的钱包又瘪了。清点起来,从中秋到国庆,再到长假末尾,我和家人一共参加了3场婚礼,加上另外3场因为时间冲突无法赶赴的婚礼邀约,我们足足送出了6个红包,每个红包的礼金,至少也有1000元。放完假上班那天,正好是工资日,看着到账的薪水,再看看上个月的信用卡账单,结余下来的钱,还不够填补这个假期送出去的一半。
总额将近万元的礼金,一份份由我亲手递出,要说一点都不心疼,肯定是自欺欺人的谎话。但是,从情理、道义上看,这几笔婚礼红包形式的人情支出,也没有哪笔是我们不该出、不必出的。6对邀请我们赴约的新人,有5对都参加过我和妻子的婚礼,送给他们的红包,只不过是还过去的人情。余下的那对,新郎是我幼时极好的玩伴,当时没请人家参加婚礼,本就是我亏心,如今故友发来请柬,岂有不“共襄盛举”、随上份子之理?
“黄金周”的名号,听着就很旺财运。不过,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一个黄金周过下来,散出去的“黄金”,往往要比赚到的多得多。每年的“十一”假期都是婚礼高峰,还有不少前两年因为新冠疫情没办成婚礼的新人,主动将这桩大事挪到了今年。而且,越是二三十岁,社交圈中正值婚龄的朋友越多,对进入社会不久,积蓄还不算丰厚的年轻人而言,简直就是一记定制款的“人情暴击”。
当然,多数情况下,参加婚礼都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而且,当代年轻人的社交习惯越来越“直”,很多人都学会了拒绝那些不熟的人发来的婚礼请柬。从理论上讲,既然结婚的都是好朋友、真朋友,给点礼金,又有什么好纠结的呢?但是,人们总说友谊无价,但在一定程度上,婚礼红包这档子事,实在太像是在给友谊明码标价了,因此难免令人难受、纠结。
给红包的人会纠结:某个老同学给1000元是不是就够了,这样对得起我们多年交情吗?那个大学舍友和我很铁,我想多给一些,可是其他舍友结婚我没给那么多,会不会“不患寡而患不均”?某个朋友的婚礼在很远的城市举办,赶过去要花不少旅费,我能不能少随点份子,或是干脆不出席,用微信多打点钱?
也别以为收红包的人就不会纠结——办过婚礼的过来人,肯定都懂个中滋味。当年某个朋友结婚,我包了2000元红包,怎么这次对方出席我的婚礼,只回了1000元?提前一个多月,就给某个以为关系很好的同学发了邀请,怎么对方不仅不出席,还只用手机发来500元礼金?还有朋友不知何故,出手特别阔气,送来的礼物价值数万、远超预期,让人不知如何报答是好……总而言之,对方给多给少,也都有让收钱者发愁的理由。
这些关于金钱的纠结,看起来很俗气。不过,亲身经历告诉我:那些与金钱无关、看似纯粹的“人情债”,可能比礼金问题还要让人头疼。我有一位朋友,结婚时邀请了一个很好的闺蜜当伴娘,还请她在婚礼现场致辞发言。结果那位闺蜜结婚时,不仅没给我那位朋友安排任何特殊角色,连请柬都是提前3天才发来的。两个人的友谊,瞬时就遭遇了一场严峻考验。还有一次,我本来都答应了要参加一场朋友的婚礼,结果当天临时有推不开的事情,只能给朋友连连道歉,但在朋友的回复中,我明显感受到他不开心了,让人心中很难释怀。
有人或许会说:既然婚礼里面有这么多麻烦事,以后改改婚俗,红包也不用给了,不就好了吗?但是,且不说传统不可能说改就改,就算真的能改,这也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牵绊变淡,未必全是好事。只要和对方关系够好,给出红包时,那种快乐的幸福感,可能远超金钱本身;收到红包时,虽然知道其中很多钱之后都要用其他形式还回去,还是会感受到大家的美好祝愿。
没人喜欢纠结,但只要这些传统习俗里蕴含的积极意义依然存在,我们就很难彻底将其放下,因此不得不学会处理各种现实场景,与复杂的人情世故同在。但是,我们可以试着用更轻盈的心态面对纠结:既然选择接受人情世故的约束,不妨少些精神内耗,把该做的事做了就好;反过来说,如果某些纠结真的令人那么难受,或者个人财政状况已经入不敷出,坦诚面对自己的内心与现实需求,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友情链接